requestId:689bb21d56eaf6.30090095.
古典生涯經驗與中國哲學創作——陳少明《做中國哲學:一些方式論的思慮》讀后感
作者:楊海文
來源:原載于《開放時代》2015年第6期
時間:孔子二五六六年歲個人空間次乙未十月廿五日丙辰
耶穌2015年12月6日
【摘要】解讀舞蹈場地陳少明傳授的新著《做中國哲學:一些方式論的思慮》,可捉住三個重點。第一,經由“有思惟價值的事務”的敞開與呈現,那些具體、生動的古典生涯經驗從覺醒中醒來,激活并煥發了人們的觀念創造與哲學創作。第二,古典生涯經驗及其豐富的意義蘊含于人、事、物的復雜關聯之間,識人、說事、觀物呼喚并直接走向新的中國哲學書寫方法。第三,剷除非哲學性傾向,皈依哲學性傾向,激活古典生涯經驗,不消哲學史研討取代哲學創作,中國哲學創作才幹由貧乏變得豐盈、由後天缺乏變得枝繁葉茂。歸結起來,“做中國哲學”實則以古典生涯經驗達成中國哲學創作,這對于發展并創新中國哲學史方式論具有別開生面的啟發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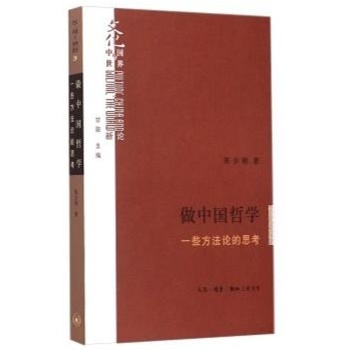
陳少明師長教師的新書《做中國哲學》,由12篇既彼此呼應、又各自獨立的論文結集而成。作者強調:“分歧的論題之間,能夠匯通當然完滿,但獨立存在的意義也不應抹殺。每一篇論文,都可以描繪一道思惟的風景線。”[1]這一提醒告訴我們:講哲學史方式論,尤其是講中國哲學研討方式論,最好不要寫成一章接一章、一節連一節的專著;其實那些以問題為中間的當下尋思與單篇寫作,既對癥下藥,又與時俱進,更能讓同業心領神會,讓愛好者領略到中國哲學無邊無際的思惟魅力。所以,我在書上把“每一篇論文”五個字圈了起來,并將《什么是思惟史事務?》一文當作我們清楚及評論《做中國哲學》這本好書的切進口。
思惟史事務從屬于歷史事務,又區別于《史記·項羽本紀》記述的鴻門宴之類事務。只要具備相應的思惟史內涵,才幹稱作思惟史事務。作者認為思惟史事務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有思惟史影響的事務”,例如李斯上秦王書、董仲舒答漢武帝問;另一種是“有思惟價值的事務”,例如孔子說的“吾與點也”(《論語·先進》)、莊子與惠施的魚樂之辨(《莊子·秋水》)。記得多年前初度讀到這一論述,講座場地線人為之一新,心頭蕩漾起茅塞頓開的智性愉悅;接著讀下往,卻又覺得有些不測,因為《什么是思惟史事務?》一文聚焦于“有思惟價值的事務”而不是“有思惟史影響的事務”。
為何一視同仁?作者做過不少出色的說明:
有思惟價值的事務,則是未經反思的范疇。這類事務年夜多不是驚六合、泣鬼神的故事,沒有令江山變色、朝代更替的后果。其人物情節能夠睿智空靈,能夠悲涼冷峻,更能夠溫和雋永,也有甚至看講座場地起來瑣碎平淡的,但都具有讓人反復品味回味的內涵。[2]
是以,其意義不是通過事務與事務之間的時空因果關系在經驗上體現出來,而是心靈對經典的回應。這種回應是跨時代,有時能夠是跨文明的;同時這也意味著,回應的方法與深度是多樣的。所以,有思惟史影響的事務的判斷是客觀的,而有思惟價值的事務,則與解讀者的精力境界及知識素養有關。[3]
對聚會場地思惟史有影響的事務同政治事務一樣,其影響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變得越來越弱。但是,有思惟價值的事務,紛歧定事后就獲得即刻的呼應,但有能夠像覺醒的活火山,在不確定的時刻迸發其氣力。[4]
這些說明本源于作者對哲學的另一種認識。百年來,中國知識界受東方影響,把形而上學當作哲學的主題,覺得哲學就該是抽象的、概念的。作者指出:既然哲學的最終目標是解釋經驗,那它就應家教當是具體與抽象的雙向通道[5]。進一個步驟說,具體的故事比抽象的概念更有沾染力。經由“有思惟價值的事務”的敞開與呈現,那些具體、生動的古典生涯經驗從覺醒中醒來,激活并煥發了人們的觀念創造與哲學創作。“假如我們的哲學,不僅僅是模擬或回應東方的思惟方法或問題,而具有本身的文明內涵,就應當努力于論述本身的歷史文明經驗。”[6]在“有思惟價值的事務”這里,我們可以說面對古典生涯經驗與面向中國哲學創作獲得了統一。
從《什么是思惟史事務?》一文開始評論《做中國哲學》這本書,只是我的做法。作者揭橥并彰顯“有思惟價值的事務”的意圖非常明確,那就是藉由古典生涯經驗的復活與詮釋,讓體現中國文明特點的中國哲學創作真正提上我們這個時代的議事日程。此時此刻,我卻意猶未足。我得在“每一篇論文”那個提醒下,走進作者極具影響的《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對中國哲學書寫方法的一種思慮》之中。
識人、說事、觀物是《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一文的三根支柱,作者寫道:
疏忽具體的個性,一切大好人均千人一面,性命會掉往活氣,世界將變得有趣。要呈現這種出色,就不克不及用概念化的目光端詳人物,而要咀嚼人物的行為細節。有個性才有人格的氣力。[7]
事務某人物行為,留給歷史學家往處理。可是,不從哲學史研討而從哲學創作的角度看,經驗的價值就紛歧樣。歸根究竟,是活生生的生涯經驗,而非哲學文獻,才是哲學創作的資源。對經典供給的經驗進行哲學性反思,事就得進進我們的視野。[8]
本來說物,繞了一圈后,問題又落到人身上。這表現經典文明中的物,也被看作無情世界中的成員,也有品格個性之分……只要領悟前人觀物的目光,中國文明中關于物質與精力的關系,中國人的世界觀,才幹獲得有深度的體會。[9]
古典生涯經驗及其豐富的意義,蘊含于人、事、物的復雜關聯之間。對于前人來說,圣賢是其榜樣,工作是其道場,萬物是其伴侶,人、事、物三位一會議室出租體、生機勃勃、生生不息。可他們不在純粹概念化的標的目的上思慮,乃至那些古典生涯經驗的文字表述零零星碎,缺乏現代人偏愛的環環相扣、足以邏輯演繹的關鍵詞匯。現代的哲學史教科書,就不把現代文獻里面的人、事、物當成真正有思惟價值的哲學問題,至少當作可有可無的注腳。從“培養一雙哲學的眼睛”出發,作者指出:
大批古典聰明就以哲理(即片斷性的哲學觀念)的形態隱身于故事之中。只不過,用抽象概念與器具體敘事供給的經驗分歧,就如一束干花與連根帶泥捧出的植物的區別一樣。哲學地思慮這些經典的敘事,有兩種分歧的方法:一種是用概念的標簽把它標本化,就像把鮮花制成干花。另一種就是扶植它,維護它的鮮活,不僅看到花或樹的姿態,還要從中想象視野更寬的風景。前者是概念的構造,后者是想象的詮釋。[10]
是以,正視經驗,不是要崩潰哲學的廣泛性品德,而是通過對人、事、物各種個案的詮釋,在具體中見廣泛,在廣度中見深度。哲學不只是經驗通往理論的單行道,而是實踐與理論雙向溝私密空間通的橋梁。以詮釋的方法,用觀念觀照探測生涯,不也是哲學的一種主要活動嗎?[11]
古典生涯經驗業經無數人的千錘百煉、涵詠體味,已是經典世界中的思惟製品,這好懂得。經典世界包含原創性作品(重要成書于晚期)與詮釋性作品(重要成書于后期),源自原創性作品的古典生涯交流經驗比源自詮釋性作品的古典生涯經驗更值得我們等待,這也好懂得。現在是全球化時代,趨同的面相越來越凸起。若何從哲學的高度來證明并讓古典生涯經驗泅渡到我們的時代與人生當中,則須做出特別的說明。基于“關于哲學的論說不是哲學自己”[12],我們也得像作者那樣承認:哲學觀念(亦即哲理)是哲學理論之母,前人有哲學但更多的是哲理;哲理絕非不夠哲學,有時候反而更合適哲學的精力,因為它面向工作本身;哲理寫照了前人的思惟方法與生涯藝術,哲理的開放與顯豁同時就是古典生涯經驗的開放與顯豁。雖然古典生涯經驗在前人那里具有逼真無疑的廣泛性,但我們若何讓它變得可懂得呢?《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一文的副標題表白,它是作者交給“中國哲學書寫方法”的理論任務。
可懂得性的目標是把深入的講座場地思惟啟發才能喚醒并凸顯出來。《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的結尾寫道:“權衡一種論說或觀點的哲學檔次,不僅在于它的廣泛性,更在于它能否深入,即具有思惟的啟發才能。否則,須生常談,即便所談是哲學,也會掉往哲學的魅力,就如時下許多教科書式的哲學理論那樣。”[13]作者的意思是說:以教科書為代表,過往的哲學史研討非但不把古典生涯經驗的廣泛性當回事,更談不上著力于它的可懂得性。這為實踐中國哲學新的書寫方法、嘗試中國哲學創作留下寬闊的用武之地。同樣是依照“每一篇論文”的提醒,《中國哲學史研討與中國哲學創作》一文有助于我們洞悉古典小樹屋生涯經驗舞蹈場地與中國哲學創作的內在關聯及其現實關懷。
百年來的中國哲學史研討,成績輝煌,缺掉也在所難免。這是我的觀察,亦是年夜多數同業的觀感。作者的基礎判斷則是:“中國哲學史研討對中國哲學創作的促進感化不年夜”,“之所以出現哲學史研討先于哲學創作這種順序顛倒的局勢,是因為現代學人談哲學的興趣一開始在于評估文明傳統,而不是發展新的學術專業”,“這種哲學史研討的標準不在哲學自己”,“中國哲學史研討的總體趨勢是越來越與哲學無關,而中國哲學創作更難有蹤影可尋”[14]。把非哲學性傾向視作哲學史研討的歧向,這是極其鋒利的洞見。
《中國哲學史研討與中國哲學創作》這篇文章有不少批評,觸及中國哲學史研討的痛處。針對先驅們常用的“以西釋中”,作者認為這類比較凡是難以做抵家,結果會像照哈哈鏡一樣:“中國哲學史研討相當長時間內做的是照哈哈鏡的任務,因為主流的作品多是從東方哲學中截取某些門戶或論題,作為解釋中國古典思惟的東西。”[15]針對新世紀最後幾年被熱烈討論的“中國哲學符合法規性危機”,作者指出:“明天關于中國傳統能否有哲學,或研討中國哲學史能否合適的質疑,恰是這種范疇錯置現象引發的后果。其實,范疇錯置不是用哲學作為參照系的問題,而是對哲學的懂得過分狹隘所形成的。”[16]讀這些批評,我們也有“恨鐵不成鋼”之感,可問題該若何解決呢?
剷除非哲學性傾向,皈依哲學性傾向,不消哲學史研討取代哲學創作,中國哲學創作才幹由貧乏變得豐瑜伽教室盈、由後天缺乏變得枝繁葉茂。在此過程中,古典生涯經驗自始自終地是其異常主要的思惟資源。朗現于經典世界之中的古典生涯經驗有能夠小樹屋多是人們所說的處所性知識,因此,相關的方式論思慮必不成少:“一種知識能否有價值,在于能否有用解釋了它的問題。哲學對特別文明或處所性經驗反思的價值,在于它可否提煉出有廣泛意義的論題,從而加深人類對本身生涯的懂得。”[17]在作者筆下,“以人生論為主題的中國哲學主流”[18]這類表述看起來漫不經心,可它與“體現小樹屋中國文明特點的中國哲學創作”[19]這一莊重承諾恰好是無縫對接的。把這兩句話聯系在一路考慮,作者對經由古典生涯經驗以達成中國哲學創作的自負才會力透紙背、呼之欲出。
以上,我們用倒敘法評論了《做中國哲學》書中的三篇文章:第一篇是《什么是思惟史事務?》,原載《江蘇社會科學》2007年第舞蹈場地1期;第二篇是《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對中國哲學書寫方法的一種思慮》,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第三篇是《中國哲學史研討與中國哲學創作》,原載《學術月刊》2004年第3期。首發時間不是、並且晚于寫作時間,更不是還要早得多的思慮時間。列出這三篇文章的首發時間,我們試圖在并不嚴格的意義上觀測作者的某段心路歷程。
先講兩個帶點考據滋味的例子。例一,“古典生涯經驗”算是第三篇文章的關鍵詞,但其第四節的標題用了“古典思1對1教學惟經驗”,文中不時也有這一表述。由“中國交流經典所包括的思惟或生涯經驗”[20],可知“生涯”與“思惟”能夠彼此替換;由“作為生涯方法的古典思惟經驗”[21],可見作者交流的本意。后來寫文章,盡管從思惟的角度勘察生涯的思慮路徑始終如一,作者傾向用的則是“古典生涯經驗”一詞。例二,第二篇文章有“思惟史事務”的提法[22],而把它細分為兩種類型,并把“有思惟價值的事務”彰顯出來,是第一篇文章完成的。以上兩個小考據天然不是為了代替義理,但或許可以映證:“思惟的風景,就展現在我們前去摸索的旅途上。”[23]
再用順敘法梳理我們重點評論過的三篇文章,作者“做中國哲學”的倡議及其思緒將變得更為清楚。從2004年發表的文章看,作者痛感教科書的非哲學性傾向斷送了哲學史研討的遠景教學場地,“更愿意把哲學懂得為挑戰既定學說或知識的思惟活動”,認為“就中國哲學創小樹屋作而言,儲存于文獻中的古典生涯經驗,更是主要的思惟資源”[24。從2005年發表的文章看,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編織出古典生涯經驗的“林中路”,識人、說事、觀物成績了古典生涯經驗的“還鄉路”,中國哲學新的書寫方法是“從古典的生涯經驗中,發掘未經明言而隱含此中的思惟觀念,進行有深度的哲學反思”[25]。從2007年發表的文章看,“有思惟價值的事務”起先與“有思惟史影響的事務”相并列,繼而獨立開來,成為懂得經典世界的生涯方法、價值信心、感情取向的基礎素材,“面對經典與面對經驗在這里就可以統一路來”[26]。歸結而言,共享會議室2004年的文章由破而立,2005年的文章綱舉目張,2007年的文章畫龍點睛,三文前后相續,勾畫了作者藉由古典生涯經驗達致中國哲學創作的學術理念。
讀這篇評論的人能夠會問:用三篇文章足以歸納綜合《做中國哲學》這本好書的豐厚內容與基礎觀點嗎?動筆之初,我就想著回應的事。作者寫過二十多篇講方式論的文章[27],為何《做中國哲學》一書僅收了12篇?這表白作者并不敝帚自珍,而是有所取舍,年夜刀闊斧地減失落了一半的篇目。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出書的論文教學集《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開卷就是這三篇文章,可見作者對它們的重視。總而言之,這三篇文章獨具匠心、涵蓋乾坤,既是講方式,更是講方式中的方式,是作者講方式論的代表性,對于發展并創新中國哲學史方式論具有別開生面的啟發意義。
讀者或許還會問:“有思惟價值的事務”這一方式論預設對于中國哲學創作最管用嗎?至多我的答覆是確定的,並且覺得《想象的邏輯——中國哲學的經典例證》一文的演繹美輪美奐。舉個例子,我長期做《孟子》研討,也常拿《公孫丑上》的“乍見孺子將進于井”說事,可在作者精到的辨析眼前,仍然禁不住自慚“思”穢。作者認為:惻隱之心紛歧定是偉年夜、高尚的善,但這種低度的善有能夠更純粹、更有廣泛性;《梁惠王上》記述的齊宣王以羊易牛,反襯出“乍見孺子將進于井”是孟子沉思熟慮的設計,共享空間如幻想中的佳麗增一分太胖、減一分太瘦,我們找不到更恰當瑜伽場地的其他例證來替換[28]。娓娓道來而又綿里躲針,八面來風而又自作主宰,作者討論“有思惟價值的事務”的文章讓人百讀不厭、回味無窮。
收縮話題,“每一篇文章”都得歸宗于“做中國哲學”的宗旨之下。第一次見到書名,先是有些不解,最終豁然開悟。同業們拿“我是做中國哲學的”介紹本身,像是家常便飯;一經作者點化,“做中國哲學”這句話雅了起來。對古典生涯經驗予以詮釋,是在做中國哲學;在詮釋古典生涯經驗的過程中實踐并實現中國哲學創作,同樣是在做中國哲學。《自序》寫道:
本書的提議是,在思惟資源方面,貼近經典文本,從古典生涯經驗中獲取題材與靈感,發掘事物的深層意義,即通過識人、說事、觀物諸多途徑,從分歧角度進進經典的意義世界。同時,還可以探討那些前人津津樂道,但現代教科書充耳不聞的意識經驗,如惑、恥、報、不忍等等,豐富我們對古典品德人格及其培養方式的懂得。[29]
在我心目中,做中國哲學的目標,不是要證明它與西學的關系,不是為了與國際接軌,也不用在意能否能在國際登場,而是向現代中國人起首是知識界,提醒經典與現代生涯的關聯,讓它的仁愛、聰明與優雅的品質,在我們的精力生涯中發揮氣力。這才是我們經典哲學任務者應當起首努力的事業。[30]
這個炎熱的夏日,我在廣州、北京漸漸地讀《做中國哲學》一書,然后在長沙鄉下的老家寫書評。閱讀是貪吃思惟的盛宴,評述是以意逆志并斷以己意。陳少明師長教師說過:“哲學沒有點金術,學習的過程就是向經典作品請教的過程。”[31]虛心學習練就個人做中國哲學的基礎舞蹈教室功。我們老家辦宴席,長者、尊者請大師開始吃飯,會說“眾來”。眾志成城凝集我們做中國哲學的操守。有此基礎功,有此操守,既基礎于古典,家教又依托于當下,我們就能做好中國哲學,搞好中國哲學創作。“做中國哲學”由口頭禪變成座右銘,年夜俗卻又年夜雅起來,則要感謝三聯書店2015年4月出書了《做中國哲學》這本好書。
【注釋】
[1]陳少明:《自序》,氏著:《做中國哲學:一些方式論的思慮》,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6頁。
[2]陳少明:《什么是思惟史事務?》,氏著:《做中國哲學:一些方式論的思慮》,第152頁。
[3]陳少明:《什么是思惟史事務?》,前揭書,第153頁。
[4]陳少明:《什么是思惟史事務?》,前揭書,第167頁。
[5]參見陳少明:《什么是思惟史事務?》,前揭書,第168頁。
[6]陳少明:《什么是思惟史事務?》,前揭書,第168—169頁。
[7i]陳少明:《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對中國哲學書寫方法的一種思慮》,氏著:《做中國哲學:一些方式論的思慮》,第122瑜伽場地頁。
[8]陳少明:《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對中國哲學書寫方法的一種思慮》,前揭書,第122—123頁。
[9]陳少明:《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對中國哲學書寫方法的一種思慮》,前揭書,第137頁。
[10陳少明:《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對中國哲學書寫方法的一種思慮》,前揭書,第144頁。
[11陳少明:《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對中國哲學書寫方法的一種思慮》,前揭書,第145頁。
[12]參見陳少明:《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對中國哲學書寫方法的一種思慮》,前揭書,第141頁。按,這是法蘭西學院思惟史傳授培里·哈度(Pierre Hadot)的觀點。
[13]陳少明:《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對中國哲學書寫方法的一種思慮》,前揭書,第145頁。
[14]陳少明:《中國哲學史研討與中國哲學創作》,氏著:《做中國哲學:一些方式論的思慮》,第70、74—75、77、110頁。
[15]陳少明:《中國哲學史研討與中國哲學創作》,前揭書,第82頁。
[16]陳少明:《中國哲學史研討與中國哲學創作》,前揭書,第84頁。
[17]陳少明:《中國哲學史研討與中國哲學創作》,前揭書,第109頁。
[18]參見陳少明:《中國哲學史研討與中國哲學創作》,前揭書,第84頁。
[19]參見陳少明:《中國哲學史研討與中國哲學創作》,前揭書,第70頁。
[20]參見陳少明:《中國哲學史研討與中國哲學創作》,前揭書,第109頁。
[21]參見陳少明:《中國哲學史研討與中國哲學創作》,前揭書,第107頁。
[22]參見陳少明:《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對中國哲學書寫方法的一種思慮》,前揭書,第128—129頁。
[23]陳少明:《兌換觀念的支票——中國哲1對1教學學的新摸索》,氏著:《做中國哲學:一些方式論的思慮》,第257頁。
[24]參見陳少明:《中國哲學史研討與中國哲學創作》,前揭書,第101、104頁。
[25]參見陳少明:《經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對中國哲學書寫方法的一種思慮》,前揭書,第113頁。
[26]參見陳少明:《什么是思惟史事務?》,前揭書,第169頁。
[27]《做中國哲 TC:9spacepos273
發佈留言